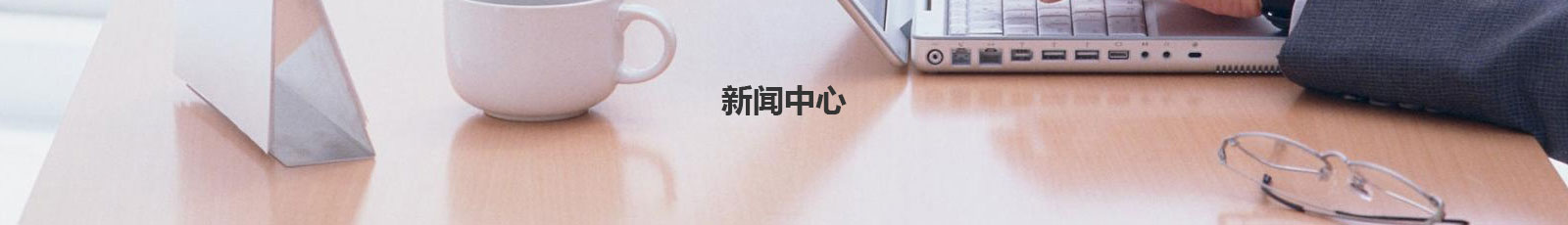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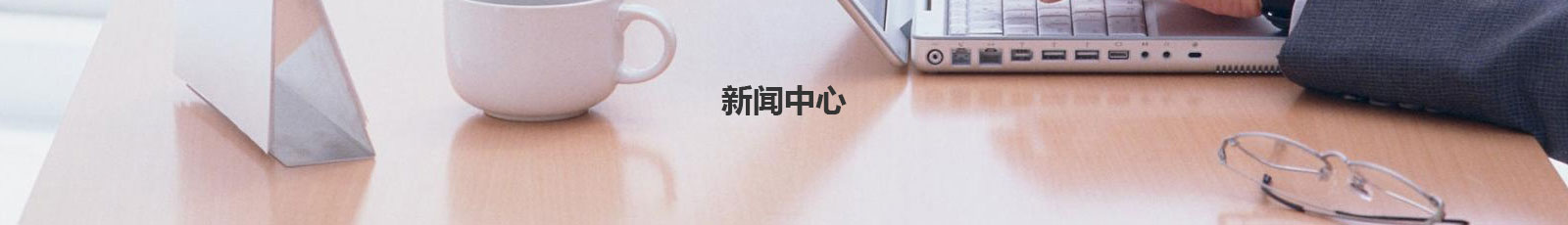
特朗普以禁毒为由对中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加征一定的关税,实则延续美国尼克松时代以来的“禁毒战争”。
2.禁毒战争在美国成为一种新的种族隔离手段,非裔和拉丁裔在逮捕和监禁比例上存在非常明显差异。
3.然而,高强度“禁毒战争”下,美国毒品问题却愈演愈烈,2023年全美吸毒过量死亡人数接近11万人。
4.事实上,奥巴马尝试着眼于“一种着重预防和治疗的方式”,但特朗普及其追随者更关注关税收入。
摘要:特朗普以禁毒为由,对中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加征一定的关税,实则延续了美国尼克松时代以来的“禁毒战争”。这一政策不仅是对外干涉的工具,更是对内种族隔离和经济剥削的手段。通过严厉的刑事制裁和私营监狱体系,美国将少数族裔变为廉价劳动力,却掩盖了毒品问题的真正根源。尽管禁毒战争持续数十年,美国毒品问题却愈演愈烈……
向来有严重“关税情结”的特朗普,刚带一批极端右翼政客回到白宫,就以芬太尼贩运为由,下令对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加征一定的关税。他提出加拿大应成为美国“第51个州”,还称墨西哥政府与贩毒集团合作,甚至称芬太尼合成类毒品来自中国。对此,墨西哥、加拿大政府都采取强硬态度,墨西哥总统辛鲍姆(Claudia Sheinbaum)谴责了他的诽谤。
在谈判后,墨西哥已同意加强打击跨美墨边境贩运芬太尼的行为,特朗普政府也同意暂停关税措施,保证努力阻止大口径武器自美国非法流入墨西哥。特朗普与墨西哥政府的下一场斗争,或将围绕美国是否能将墨西哥贩毒集团列入恐怖组织名单展开——此举将有利于美国发动单方面军事行动。
尽管特朗普史无前例地代表着美国极右翼浪潮,但是,无视其班底成员面临的法律指控、打压新闻界、以“禁毒战争(War on Drugs)”作为政治筹码,并非他的首创,而和因水门事件辞职的尼克松一脉相承。特朗普的“芬太尼关税”所代表的美国禁毒战争,由尼克松在1971年首创,被各届政府以不同方式继承,牵动着打压少数族裔、军事干涉其它国家等诸多议题。
二战后,出于抵抗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文化的压抑、对越战及其它军事干预的反对等,美国的中产阶级经历了从“垮掉的一代”到“嬉皮士”的反主流文化探索。在阿片类药物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上世纪六十年代,药物滥用慢慢的变成为新的社会问题,并与对美国主流政治的反叛被联系在一起。1971年,尼克松宣布毒品滥用是美国“头号公敌”,提出了“禁毒战争”这一术语,主张严厉的刑事制裁。从此,毒品战争在美国成为一种正式的政治想象。
尽管严厉的立法和刑罚降低了当时的毒品滥用率,尼克松的原始动机却备受怀疑。1994年,他的国内事务顾问、因水门事件入狱的埃利希曼(John Ehrlichman)在采访中承认:“尼克松的白宫有两个敌人,反战的左翼,和(争取平权的)黑人。我们没法直接给他们定罪,但我们大家可以让公众把嬉皮士与、黑人与联系起来,然后再把他们当罪犯对待、干扰他们的社群。我们大家可以逮捕他们的领导者,抄他们的家,打断他们的集会,在晚间新闻中诋毁他们。我们大家都知道自己在毒品问题上撒谎了吗?我们当然知道了。”
如何理解毒品战争是新的种族隔离?1970年,因持毒、吸毒等被逮捕的美国成年人数量是32.23万人,这一数字在2000年已飙升至137.56万,非裔和拉丁裔在其中的数量不成比例地上升。2001年,美国政府监禁非裔男子的速度大约是南非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监禁黑人男子的四倍;2012年,监狱中的黑人男子数量已超过1850年被迫沦为奴隶的黑人男性人数,即逼近美国奴隶制的鼎盛时期。
为何美国黑人和白人的非法毒品使用率相当,逮捕和监禁比例上却存在非常明显差异?在立法上,里根继尼克松之后启用的强制最低刑期(Mandatory Minimum Sentence)包含着针对非裔的不公。比如,使用生理危害相当的粉状可卡因和块状可卡因,前者纯度高、价格昂贵,受众是中产白人,后者因杂质多、价格低,消费主力是贫困黑人;对于同样的刑期,后者的入刑重量标准仅为前者的1%。在执法和司法上,研究表明,出于种族歧视等因素,美国警察在执法中更倾向于拦截搜身黑人而非白人;在审前拘留和保释金机制下,来自贫困阶层,更缺乏经济和法律资源的黑人,也更加容易被迫认罪、更易困于漫长的审前拘留。因为系统性的种族歧视,相比美国白人,禁毒战争下的黑人面临更高的入狱概率和更长的刑期。
在奴隶制结束后,实行种族隔离的吉姆克罗法(Jim Clow Laws),对富裕黑人街区的种族屠杀,排斥少数族裔社区、拒绝为其提供城市服务的“红线政策(Redlining)”等,本就剥削着黑人社群的社会和经济资源,迫使他们生活在更低经济阶层;而始于七十年代的禁毒战争,成为最后一根稻草:倾斜性地逮捕少数族裔,将贫困黑人社区的形象和毒品捆绑在一起。出狱后的少数族裔难以融入社会、面临更严峻的歧视和更稀缺的就业资源,其社区状况进一步下滑,毒品产业更易植入这些社区,形成恶性循环。
什么给了保守政府长期发动禁毒战争的动力?答案是服刑人员作为廉价劳动力给私营监狱带来的高额利润。在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共生体中,资本主义生存的基础在于种族主义对人性价值不平等的区分,这一视角能帮助理解禁毒战争与监狱-工业综合体(Prison-industrial Complex)的关系。著名监狱研究者吉尔摩(Ruth Gilmore)在她的著作《金色古拉格》中就阐释了美国监工综合体的剥削方式。在私营监狱众多的美国,无法保障自身权益的囚犯往往被作为低廉劳动力,以极低的工资为大公司生产,再以工资购买监狱内价格高昂的服务。监狱业的利润催生了代表其利益的游说集团,鼓励共和党议员建立更多监狱,以此增加警察经费和降低失业率,收获政治利益。此外,在共和党选区建立监狱以保证选区的统计人口,以及剥夺少数族裔的投票权利,均有利于共和党的选举优势。一言以蔽之,禁毒战争有利于美国政府合法地将少数族裔变为廉价劳动力,并预防他们变革所在选区的政治关系。
然而,“新型种族隔离”的真相,无法打动特朗普的文化极右翼拥戴者,以J·D·万斯为代表的,支持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的青年男性。2023年,美国白人的贫困率是9.5%,而黑人和西语裔人口的贫困率分别是20.6%和16.6%,从美国社会结构中根除种族主义道阻且长。但是,对文化极右翼来说,数十年来发生在美国和全球的种种抗争,如曾被剥削的国家追求发展的平等、少数族裔和女性追求权利的平等等,都是“颠覆美国的”、“追求特权的”。
在他们看来,落后的国家是文化和制度失败的,穷人是不够努力的,少数族裔是懒惰的,平权是要求特权——不承认历史中的剥削,就不需要面对身份认同的恐惧和随之而来的责任。从“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到“黑命贵”的歪曲翻译,正是一种对少数族裔“特权”的极右翼想象;为“加拿大是美国的一个州”和“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利坚湾”欢呼,也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特别是白人男性中心主义的终极梦想。
在这种情形下,作为一种政治建构的禁毒战争,不仅是美国右翼对内治理的手段,也是对外干涉的工具,特朗普的加税理由仅是其中的冰山一角。
自1971年以来,美国在墨西哥和南美的军事行动中投入数十亿美元,打击贩毒集团和走私者。但这种打击是有选择的——八十年代,中情局在尼加拉瓜扶持的右翼武装就向美国走私可卡因以获取资金。持续数十年的哥伦比亚内战在2016年终于迎来和平协议,而此后第一届特朗普政府和哥国极右翼杜克(Ivan Duque)政府的禁毒战争合作,忽视区域人权和战后重建,对潜在的毒品作物种植区进行无差别清扫,逼得一些前武装成员又重返战场。
无数类似的例子表明,在美国军火不断流入拉丁美洲、美国国内继续以刑罚手段进行毒品治理的情况下,禁毒战争更像一个永不终结的借口,而非行之有效的措施。
据美国疾控统计,2023年,全美吸毒过量死亡人数接近11万人,其中约69%死于芬太尼。
镇痛能力比强30至50倍的芬太尼,以及其代表的新兴毒品,其进化速度超出了立法及药检的速度,导致管制格外困难。面对禁毒战争的失败,美国进步人士看待阿片滥用危机的视角,正从尼克松等人推崇的刑事定罪,转向公共医疗治理。事实上,奥巴马在其执政时期就尝试着眼于“一种着重预防和治疗的方式”。第一先考虑个体本身,而不是其刑罚,也是更科学的毒品政策:只有加强对药品滥用者的包容化支持,才能鼓励他们自主寻求干预和治疗,降低相关传染病流行率。只有为戒毒者提供重新融入社会的指导,才能防止其再次落入贫困和毒品的陷阱。也只有教育、禁毒与治疗的多方面配合,才能线年底,联合国也呼吁转变毒品政策。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蒂尔克(Volker Turk)表示:“刑事定罪和禁令未能减少毒品使用,也未能遏制与毒品有关的犯罪。我们辜负了社会中一些最脆弱的群体。”
然而,当禁毒战争是一种称手的武器,特朗普及其追随者更关注的,或许是关税收入,而不是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
上一篇: 伦敦达尔文墓遭环保抗议者喷漆